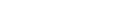酷夏来了,电力企业怎么解决困局
困局之一:“降碳减排”道阻且长
单位产品能耗高、投入产出率低的“消化不良症”在我国能源电力企业中很普遍,粗放型发展路子仍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明显改观。当前能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能源电力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行业和我国碳排放的“第一大户”,能源燃烧和电力生产在我国温室气体排放中占据着绝对主体地位,其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既是确保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和蓝天保卫战的重要支撑,又是实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重要内容。
因此,能源电力企业的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低碳清洁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生产方式转变的重要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双碳”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变革,绿色生产、循环发展、低碳经济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正确处理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个体与集体、短期与长期的关系。
目前,一些能源电力企业纷纷确定了自己“双碳目标”的完成时间表和路线图。譬如,国家电投、三峡集团承诺在2023年实现碳达峰,国家能源集团、大唐、华电、华润计划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中节能、国投也分别计划在2028年、2030年实现碳达峰。另外,三峡集团作为首家公布碳中和时间表的央企,计划在2040年实现碳中和;中节能也提出力争在2040年左右实现运营碳中和,2050年实现供应链碳中和,2060年消化历史化石燃料碳排放。但要想按时交上完美的“答卷”,肯定不是件轻松的事,面临重重困难,突出表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一是政策困境。虽然早在1997年我国就颁布了《能源节约法》,但同欧洲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碳中和、碳资产碳交易等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缺乏高层级的法律支持,相关的配套措施也不健全,完善的财税激励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仍有待搭建,这给能源电力企业碳排放权质押、碳租赁、碳衍生品等碳交易活动制造了不少政策障碍。
二是技术困境。虽然我国在碳减排方面的技术储备近年发展相对迅速、进步较为明显,但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例如,电化学储备技术大多掌握在欧美企业手里,氢燃料电池70%的专利被日本企业控制,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虽与国际整体发展水平差距不是太大,但仍处于工业化的示范阶段、部分关键核心技术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三是经济困境。绿色低碳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非常难,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就拿CCUS净减排成本来说,我国传统煤电厂、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IGCC)电厂、天然气循环联合发电(NGCC)的避免成本大约分别为 60 美元 /t CO2、81 美元 /t CO2、99 美元 /t CO2,在目前燃煤燃气价格居高不下、火电亏损严重的情况下,这笔费用对于绝大多数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的火力发电企业来说也是难以承受之重。
四是环境困境。从资源禀赋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具备丰富的风电、光伏、水电等清洁能源资源,但生态更加脆弱,过度无序的开发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新材料和新化学品在新能源加工、生产、运维等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也会产生大量对环境有害的物质,甚至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回收利用和报废处理也要花巨大的费用代价的。
困局之二:产业转型步履维艰
船大难调头的“头痛病”在能源电力企业历来已久。“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曾是不少传统能源电力企业的“通病”,也留下难以治愈的“后遗症”。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我国经济发展放缓和新冠疫情久拖不停的多重压力下,一些能源电力企业在经济的寒潮中被冻得瑟瑟发抖,陷入了“转型找死,不转型等死”的魔咒。
往哪儿转?怎么转?是许多传统能源电力企业一直都在思考和苦苦追寻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推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能源电力市场的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挤压,早已从“红利时代”进入到“微利时代”,成为竞争白热化、业务同质化、经营微利化的一片汪洋“红海”,导致传统能源电力企业更加步履维艰、雪上加霜、难逃厄运。即便国家提出“新基建”战略和“东数西算”工程,出现一些新的“蓝海”,也恐怕只是个“浅滩”,“远水解不了近渴”,难以支撑起规模庞大、数量惊人的能源电力企业转型发展的需要。
因此,所谓的新能源、新电力、新业态、新模式成为了不少企业眼中的“蓝海”和“香饽饽”,引得各路英豪“竞折腰”,蜂涌而至、纷纷沓来,既便头破血流也要千方百计挤进这个“赛道”,好不容易捕捉到了一丝的机会,但因为市场竞争激烈、各类成本上涨、经营效益不佳,也只能解决一时之痛,难以从根本上破而新生。
目前,传统能源电力企业转型升级面临以下三大“痛点”:
首先,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能源电力企业的“老套路”已经行不通了。作为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国有“老企业”,能源电力企业职工数量庞大,历史包袱沉重,总体素质较差,哪怕任何一个细小的变革都会带来巨大的波澜,还有企业原有的组织架构、知识结构、产业体系、发展路径变成了转型路上的种种“挡路虎”,加上管理层思想僵化,经营观念守旧,跟不上时代新潮流,企业想要转型发展、主动求变,似乎更是难上加难。
其次,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生产力的底层早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这个风云变幻、瞬息万变的时代,只有掌握新技术、擅握新机遇的企业才能成为财富的“新贵”、市场的“赢家”和时代的“弄潮儿”,否则就会被竞争对手打败、被迅速地淘汰出局。
再者,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为传统能源企业的转型升级增添了新的变数。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疫情之后能源电力企业面临的国际经营环境将会更加恶化,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中美“脱钩”的风险持续加大,俄乌冲突的“后遗症”逐步显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将会从政治、经济、外交领域对我国进行全面打压,中外能源电力企业合作难度在持续地上升,不仅会加剧能源电力企既有产业转型的速率、频率、烈度,而且为今后产业转型增添了诸多新的变数、障碍和考验。
困局之三:“煤电顶牛”知易行难
煤电“顶牛”是煤电改革不到位、不彻底而出现“内分泌失调症”的“副产品”,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挥之不去的一片阴霾。其产生的根本在于市场的“煤”和计划的“电”发生顶撞,难以有效衔接,导致一边赚得金钵满盆、另一边亏损累累,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随时会劈下来似的,让以煤作为燃料的企业苦不堪言。
最近一次发生煤电顶牛的现象应该是2021年下半年。自当年10月开始,煤炭价格逐渐脱离供求基本面、短期内大幅飙升并屡创新高,造成燃煤发电行业亏损严重,煤企和电企的业绩再现“冰火两重天”,全国多地发生电力供应短缺情况和限电、限产现象,既影响到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也损害了经济平稳运行,还更加凸显了煤电对保障电力供应安全的兜底作用。据有关权威机构测算,2021年因电煤价格上涨、电力企业保供导致煤电企业的燃料采购成本额外增加6000亿元、亏损超1000亿元,陷入“越发越亏”两难窘境。
不可否认,煤电作为我国的主力电源,长期以来发挥着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应急调峰、集中供热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需要继续发挥煤炭在我国能源中供应中的主体作用以及煤电在电力系统中的兜底保供和调峰调频等作用。因此,在“双碳目标”下,如何科学把握好煤电的发展定位、有效解开煤电发展的困境、切实避免煤电发展陷于恶性循环并从根本上解决“煤电牛顶”现象,越来越成为业内外不少有志之士主动思考和苦苦探索的一个重大而又急迫的问题。
为有效化解煤电顶牛的矛盾,国家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可谓动作频频。不少地方政府尤其是沿海缺电省市加大煤电价格的浮动范围,还有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意在坚持市场煤的基础上,明确合理区间内煤、电价格可以有效传导,实现了与燃煤发电“基准价+上下浮动不超过20%”电价区间的有效衔接,而超出价格合理区间将及时调控监管。《通知》之所以获得业内广泛认可,是因为坚持市场化改革和法制化手段相结合的方式,理顺煤、电的价格关系,为解决“煤电顶牛”难题开出一剂良方。
然而,世界上并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从根子上讲,煤电顶牛的本质在于电价形成机制没有真正理顺,即煤价随行就市、电价却牢牢地被锁死,造成价格的传导机制堵塞不畅。因此,如果要想从根本上解开煤电牛顶的难题,治本之策在于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在优化电力资源配置和促进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中的作用,借助煤价、上网电价、用户电价通过市场化方式“三价联动”的方式,让市场的“煤”与市场的“电”有机衔接起来,有效实现“上限保电、下限保煤”的总要求,既不能让煤炭价格成为“脱僵的野马”,也不能发电企业“独吞煤价上涨的苦果”,更不能让用户来承担改革的成本,还要让政府监管切实做到“到位不越位、补位不缺位”,最终达到“治标又治本”的目的。
困局之四:产能过剩难题待解
企业总体规模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差,能源电力企业的“巨人症”、“虚胖症”不仅体现在经营体量上、资产规模上和人员数量上,而且体现在过剩产能上、业务范围上和管理层级上。经过持续多年的“跑马圈地”和无节制地高速发展,我国能源电力行业的总供给已由短缺时代转入总体过剩时代,尤其是传统的煤电产能过剩相对突出,能源建设市场供过于求,中低端电气设备严重饱和。
根据最新统计,截止到2022年3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4亿千瓦,其中煤电装机达11.1亿千瓦,一季度煤电的发电量占比超过62.8%,利用小时仅1169小时,出力明显不足。造成产能过剩主要是电力结构产业不断恶化,尤其是传统电力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清洁能源和新兴能源投资仍然滞后,成为掣肘能源电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恶瘤”,让不少企业在传统产能过剩的泥潭里难以自拔,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发电侧来看,我国一方面“窝电”严重、一方面又“野蛮”生长,造成严重的低效、无效投资,煤电装机规模偏高,发电利用小时逐年降低,按煤电正常发电利用小时5500小时计算,全国火电机组过剩大约在1.5至2亿千瓦;而新能源装机虽然近几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但发电量仅占14%左右,并且集中在我国经济不发达的“胡焕庸线”以西的地区。
二是从建设侧来看,受能源电力转型的影响,传统电建市场的空间不断萎缩,“僧多粥少”的状况越来越突出,电力建设任务严重不足,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电力建设市场供需失衡的问题一直难以扭转并有持续恶化的倾向。仅我国两大电建巨头中国电建和中国能源的施工能力就差不多能够满足全球传统电力建设任务的需要。
三是从装备侧来看,电源设备尤其是火电设备的行业集中度虽然相对较高,但产能过剩非常严重;输配电设备领域细分行业多,在高技术领域国内领先企业相对较少,而在中低端领域的企业数量较多,竞争较为激烈;电气设备行业目前除少数几家头部企业有一定的竞争力外,大多数在产业链上下游中处于弱势地位,产能过剩也非常突出,生产严重不饱和。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电力需求预计会保持低速增长,年均增速在2.5%左右,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0%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39%。由此可见,我国能源电力的总体发展的黄金期已过,但清洁能源正处于快速成长新阶段,如果不能把握好发展的节奏,仍然盲目、无序、不计后果地加速发展,再过几年以后,极有可能又陷于新一波的“产能过剩”。
因此,有必要从供需两端入手,下大力解决能源电力产能过剩问题:一方面在供给侧方面,要坚持优化增量与调整存量并举方式,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的基础上,大力推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努力拓展电力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另一方面在需求侧方面,加大电能替代与绿色消费导向等多措并举,全面推动节能降耗降碳行动,提升终端用能低碳化、电气化水平,不断培育能源电力消费新的增长点。
困局之五:数字转型任重道远
信息传导不顺畅、“内卷化”现象严重、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脑神经梗塞症”是制约国有企业创新驱动的真正“结症”、也是导致企业管理运营效率低下的关键所在。在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大格局下,越来越多的能源电力企业深刻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极端重要性,将其视为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筑牢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开始加速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然而,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绝不仅仅只是引进一套工具、打造一个系统就可以实现的,除需要必要的“真金白银”硬件投入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软件建设上下功夫。
能源电力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充分了解企业数字化的底层逻辑,真正构建从上到下的数字化思维模式,达成高效的数字化共识需要,真正扫除以下三大“挡路虎”:
数字化的思维体系尚未建立。绝大多数能源电力企业仍停留在传统的经营思维模式上,很少能够用数字来探索和思考事物,用数据来发现问题、洞察规律、探索真理。2021年4月麦肯锡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率仅20%,失败率高达80%,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同认识有关,没有形成数字化的思维方式,没有真正实现从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的转变。
敏捷的组织体系尚未普及。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势必引发企业组织结构、工作模式变革,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并不适应,否则就会酿成“大灾难”。其实,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并在于技术和设备的先进性,而是组织变革使之具有敏捷性和适应性,因为大型企业的组织要远比科技要复杂得多,更多的是领导层面临的挑战,而非技术难题,组织才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所在。
数据价值的挖掘很不充分。电力即算力,数据对能源电力系统越来越重要,而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能源网络和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对数据资产管理的要求不断提高。但受制于采集、统计、管理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现阶段能源电力数据的外部应用场景非常有限。因此,如何将“沉睡中”的能源电力数据唤醒,并作为资产挖掘其价值早已成为行业普遍共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建立健全能源电力数据使用的制度依据、明晰电力数据管理权责利界定,摘掉戴在能源电力企业头顶的“紧箍咒”。
总体来看,能源电力的数字化关系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关乎着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能否顺利实现。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能源电力的发展存在着“不可能三角”的难题,即能源系统的安全性与用能的经济性及清洁绿色的要求难以相互兼顾。而随着能源电力的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新型电力系统的建立,就有条件、有能力把这种不可能变成了有可能。因此,如何打通能源电力企业与部门之间、能源电力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数据壁垒和数字鸿沟,形成数字转型和能源转型要相互支撑、携手共进的局面,这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意识问题,更重要的是机制问题。